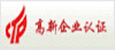您當前位置:首頁 > 商標注冊申請 > 行業新聞 > 天津同仁堂陷商標侵權訴訟
天津同仁堂陷商標侵權訴訟
“云母屏開,珍珠簾閉,防風吹散沉香。。。。。。烏頭白,最苦參商。當歸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黃。”,辛棄疾在這首不足百字的滿庭芳靜夜思中,居然使用了云母、珍珠、防風、烏頭、苦參、當歸、茱萸、菊花等共25種常用中藥名,不愧是詞中之龍的經典之作。
日常生活中提到中醫藥,很多人可能會立刻想到,生產六味地黃丸的上市公司北京同仁堂,這家公司系樂鳳鳴于1702年創立的同仁堂藥室的基礎上所開設的同仁堂藥店發展而來。
而本文著重討論的,是目前正在申請創業板上市的天津同仁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津同仁堂或發行人)。值得注意的是,發行人并非北京同仁堂的子公司或參股公司,兩者之間也無其他關聯關系。所以,此同仁堂,非彼同仁堂。
那么,發行人和北京同仁堂這樣的中醫藥大咖同名,難道就不會引起知識產權方面的糾紛嗎?實際上,糾紛已經發生了,而且北京同仁堂對發行人提起的這項重大訴訟,可能已經構成發行人上市的最大障礙之一。
除此之外,發行人還可能存在虛增收入和利潤,未來多項政策可能嚴重影響收入和盈利,以及大額關聯交易和大額分紅可能引發的資金體外循環等嫌疑,都可能成為其上市的障礙。估值之家將對這些問題,做詳細分析和解讀。
1
深陷重大訴訟風險,如敗訴將嚴重影響盈利和持續經營,或構成上市障礙
在分析北京同仁堂對發行人的這項重大訴訟之前,估值之家首先要對發行人和北京同仁堂分別做基本介紹:
(1)發行人系由張彥森家族控股的民營企業,張彥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計持股59%,張彥森之弟張彥明持股1%,麗珠集團持股40%。
(2)發行人的主要收入和盈利,均集中于腎炎康復片、血府逐瘀膠囊和脈管復康片這三大主營產品,三者合計占到最近一期營業收入的88%,毛利的91%。比如:
占比最大的腎炎康復片,用于治療泌尿系統疾病,占營業收入的39%,毛利的40%;
占比第二的血府逐瘀膠囊,用于治療心腦血管疾病,占營業收入的35%,毛利的36%;
占比第三的脈管復康片,主要用于治療糖尿病導致的周圍血管疾病,占營業收入的14%,毛利的15%。
(3)發行人主要采用經銷模式銷售,由經銷商銷售至全國各終端市場。
(4)而北京同仁堂,則是隸屬于北京國資委的國有獨資公司,生產經營多種中醫藥產品,旗下已經擁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和同仁堂國藥,實力遠超發行人。
在了解了兩者的基本情況后,我們重新聚焦回到這項重大訴訟上。
招股書顯示:
“2021年8月6日,原告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將公司作為被告之一,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出訴訟,訴訟案由為“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對公司訴訟請求為:
1、停止侵害原告注冊商標專用權;
2、立即停止使用‘同仁堂’字號、變更企業名稱,變更后的企業名稱中不得含有‘同仁堂’或者與‘同仁堂’構成近似的字樣;
3、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
4、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費用5000萬元;
5、承擔本案訴訟費用。2021年8月12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受理了該訴訟。
2021年8月20日公司收到《民事案件應訴通知書》((2021)京73民初959號)。”
北京同仁堂認為:發行人未經許可擅自使用與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冊商標高度近似的侵權標識,并通過企業名稱文字突出使用、虛假宣傳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冊商標專用權等權利,并構成不正當競爭。
由此引出本案的兩大焦點:
1)發行人是否有權使用“同仁堂”文字?
(2)發行人使用的商標,和北京同仁堂的注冊商標是否高度近似并足以引起混淆?
對于第1個焦點,發行人認為基于歷史原因有權使用“同仁堂”文字,“發行人的企業名稱已經依法取得登記機關的核準,合法享有企業名稱權。發行人的企業名稱中“同仁堂”的企業字號是其前身自清朝時期開始使用,沿用至今,在1994年及2006年兩次被相關部門認定為中華老字號。發行人目前使用的企業名稱、字號及簡稱均是公司基于其特殊的歷史淵源,在合理正常的范圍內善意誠信使用”
但實際上,兩者的前身在歷史上已經就“同仁堂”的字號使用權,有過多次訴訟:
早在1852年,發行人的前身“張家老藥鋪”,未經北京同仁堂許可,自行更名為“天津同仁堂”,結果被北京同仁堂起訴侵權。最后天津同仁堂敗訴,被判決不能賣北京同仁堂的藥品,也不允許其使用北京同仁堂的商標,僅允許其使用“天津同仁堂和記”的名稱。
幾十年后,雙方為了“同仁堂”字號,易地再戰于天津。1907年,天津審判廳開庭審理并判決: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號,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號經營。
從歷史記錄來看,天津同仁堂在字號使用權的糾紛中,總體處于較大劣勢。
雖然第1個焦點,具體還將取決于法院的判決,但總體而言,北京同仁堂基于歷史淵源和現實實力,明顯比發行人更占上風。
對于第2個焦點,商標法第57條第二款明確規定: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或者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容易導致混淆的,屬于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
由于,發行人和北京同仁堂都經營中藥類產品,而且在紫雪散等產品上還有重疊,所以符合該條款規定的相同或相似商品這一前提,這樣一來,本案的關鍵就在于,發行人的商標是否和北京同仁堂相似,并足以引起混淆。如果商標相似并足以引起混淆,那么發行人很可能構成侵權。
發行人當然極力否認兩者相似。招股書顯示:“發行人在目前的產品包裝上主要使用“太陽”商標和“天工”標識,未使用包含“同仁堂”的相關文字、圖形或者組合,其所使用的商標、標識與北京同仁堂所使用的“同仁堂”注冊商標存在顯著區別,不容易導致混淆誤認。”
但按照法律規定,混淆的判斷標準應當以普通消費者的“一般注意力”為標準,即分別觀察兩者商標后,憑借記憶比較兩商標之間最顯著、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斷兩商標在整體上是否給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進而判斷消費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標識的產品時,是否會直接誤認為該商品就來源于北京同仁堂。
所以,商標是否相似,還包括整體印象和消費者認知等很多因素,并不局限于“同仁堂”的文字或圖形是否存在。所以,除非得到法院的最終判決,否則發行人的敗訴風險依然明顯存在,無法忽視。
發行人顯然也意識到了,消費者認知對于判斷兩者商標是否相似的重要性,所以特意做了補救性澄清。
招股書顯示:“發行人主要產品均為處方藥,主要終端為公立醫療機構。對于公立醫療機構銷售的處方藥,消費者無法通過自行判斷、購買和使用,需憑處方購買;執業醫師開具處方主要根據患者具體情況以及藥品適應癥,而非藥品品牌。不同于普通消費者,執業醫師具有一定的醫學知識和臨床經驗,在治療和藥物選擇方面通常能夠做出專業的判斷。通過對9家三級甲等醫院的32名主任及副主任執業醫生訪談,受訪談人均能明確區分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發行人的此處澄清的邏輯可以歸納為:
(1)發行人的主要產品是處方藥,所以只有執業醫師有選擇權,而普通消費者沒有選擇權;
(2)所以不需要普通消費者能夠明確區分發行人和北京同仁堂,只要執業醫師能夠明確區分即可;
(3)發行人通過走訪9家三甲醫院的32名執業副主任以上醫師,得到了100%的驗證結果。
但其實發行人的邏輯中有2點明顯不當:
(1)處方藥具體還分為單軌制處方藥和雙軌制處方藥,百度百科顯示:
單軌制處方藥:指的是只能憑醫師處方才能銷售的處方藥,主要指抗菌藥物,包括抗生素和磺胺類、喹諾酮類、抗結核、抗真菌藥物。發行人的3種主要產品,顯然不屬于抗菌類藥物,也就不屬于單軌制處方藥。
雙軌制處方藥:則指也可不憑醫師處方即可銷售的處方藥。發行人的3種主要產品,顯然屬于雙軌制處方藥,消費者不需要醫師處方,也可以自行購買。
出于謹慎,以占比最大的腎炎康復片為例,估值之家進一步查閱了京東商城等主流網購平臺,結果發現多家商戶都在京東商城平臺上銷售發行人的產品。具體請見下圖。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所以,普通消費者可以自行選擇是否購買發行人的產品,其對兩者商標的認知是否明確,也就具有了法律上的重要性。此為發行人邏輯明顯不當之一。
(2)發行人通過走訪9家三甲醫院的32名執業副主任以上醫師,得出的結論不具有可靠性。首先,抽樣對象的選擇方法沒有說明,是否僅選擇和發行人關系友好的醫師,所以抽樣對象不具有公允性。其次,抽樣對象要求副主任醫師以上,排除了更多數量的普通醫師,所以抽樣對象也不具有代表性。此為發行人邏輯明顯不當之二。
另外,估值之家還找到發行人另一種理論上規避商標侵權的可能性,這有利于發行人。出于嚴謹性和完整性,估值之家也必須分析討論。
如果發行人通過消費者不斷使用其產品,在市場上積累了相當的知名度,并且其聲譽足以高到可以將發行人與北京同仁堂區分的程度,則發行人即使突出使用其字號,也并不會導致消費者混淆,從而也就不構成商標侵權。此時,發行人還可以將“天津同仁堂”作為未注冊商標繼續使用。
但如果發行人未能達到上述知名度,則發行人不但不能突出使用“同仁堂”的字號,就連正常使用行為都應考慮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比如招股書中的例子:發行人因元胡止痛片中的有毒物質金胺O超標,被罰沒31萬元。如果此時發行人正常使用“同仁堂”的字號,但其與北京同仁堂的區別不明顯,足以被消費者混淆,那么就構成了不正當競爭。因為消費者有可能會以為是北京同仁堂的產品出現了質量問題,從而損害了北京同仁堂的正當利益,從而構成不正當競爭。)
但遺憾的是,按照對現實情況的認知,發行人的知名度顯然并未達到如此高度,而且發行人已經被起訴,在庭審前繼續發展足夠知名度的時間也遠不夠,所以顯然無法以此規避商標侵權的風險。
所以,綜合上述所有分析,發行人對于這項重大訴訟,不但沒有穩操勝券,相反還明顯處于下風,其敗訴的風險不容小覷。
那么,如果發行人敗訴,又會遭受哪些后果呢?
北京同仁堂對發行人的訴訟要求中,后果最嚴重的應屬第2項和第4項。
對于第2項,發行人如果敗訴,后續將無法使用和“同仁堂”相同或相似的字號和企業名稱,這意味著發行人將不能再以同仁堂的名義對外經營,也不能再以同仁堂的名義為品牌背書,更不能以同仁堂的名義再銷售其任何產品,這將對發行人的收入、盈利和營銷渠道都會產生巨大打擊,對發行人的企業形象、品牌和營銷也都將是滅頂之災。
而對于第4項,發行人如果敗訴,將承擔5000萬元的賠償,約占發行人最近一期凈利潤的21.4%,損失可謂巨大。
當然,發行人一旦敗訴,其他幾項訴訟要求帶來的損失也并不小。
比如第1項,停止侵害原告注冊商標專用權,意味著發行人目前的商標不能繼續使用,更換新商標很可能會引起營銷渠道的混亂和產品召回,以及患者的困惑和抵制棄用,最終造成業務收入和盈利的下降。
再比如第3項,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也意味著發行人現有產品,只要包裝涉及到同仁堂字號或者相似商標,也都將無法繼續銷售,至少需要全部更換包裝。而考慮到藥品特殊的安全性,如果無法更換包裝的則必須銷毀。這些產品,既包括尚未出庫的存貨,也包括經銷商已經采購尚未銷售,發行人因此需要召回的。涉及的數量越大也意味著發行人的損失越大。
所以,毋庸置疑,如果發行人敗訴,將面臨釜底抽薪般的巨大損失,對其持續盈利能力和持續經營能力,都將造成嚴重不利影響。而且,如果敗訴發生在發行人上市后,所有投資者都將被迫共同承擔這一巨大損失。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在上市后暴雷,從而損害投資者利益,證監會在2019年的首發業務若干問題解答中,已經明確規定:“對發行人業務經營或收入實現有重大影響的商標、專利、專有技術以及特許經營權等重要資產或技術存在重大糾紛或訴訟,已經或者未來將對發行人財務狀況或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屬于存在對發行人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不利影響的情形。
簡單來說,就是監管部門不允許“帶雷過安檢,而危害整車投資者”的情況,可以因此而否決上市申請。
所以,發行人的這一重大訴訟,一日未出結果,其上市就一日存在重大障礙。而考慮到知識產權訴訟一審、二審的較長流程,以及重審再審的可能性,預計發行人的上市之路會非常漫長。
山重水復疑無路之下,如果發行人能和北京同仁堂達成妥協得到撤訴,才不失為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明智之舉。
2
銷售收入和利潤異常增長,卻和多項數據背離,存在虛增可能性
招股書顯示,報告期內,發行人不僅實現了營業收入和毛利的逐年增長,而且增長率也均實現了每年翻倍,形勢喜人。具體請見下表。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但是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一個奇異現象:發行人每年收入的增長率和毛利的增長率幾乎完全一致,而毛利率幾乎像時鐘發條一樣,精準地圍繞著82%做微小波動。
出現這種奇異現象,有兩種可能性最大:要么發行人錨定了82%的毛利率再根據成本決定銷售價格;要么數據是硬湊出來,增長是不真實的。
按成本加較高利潤率的方式定價,要求發行人具有相當強的市場壟斷地位和議價能力。但發行人的三種主要產品,在市場上均存在多種同類競品,替代性很強;而且發行人主要客戶的體量和實力,也要大于發行人,比如中國醫藥和上海醫藥,都是市值幾百億的上市公司,其議價能力不可能弱于發行人。
據此,發行人基本不可能實現以成本加成方式定價,相反其銷售價格必須隨行就市,因此不可能如此精確地維持固定的高毛利率。
如果懷疑發行人的收入和利潤數據有虛增,但僅憑上述這一個疑點,顯然難以令人信服。估值之家又比較了發行人以下數據的變化趨勢,均完全與營業收入和利潤的大幅增長趨勢相反,所以非常可疑。
(1)發行人的員工人數逐年減少,比如2021年減少了15%,但同期的營業收入和利潤反而都增加了約24%,兩者差異接近40%。具體請見下表。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招股書從未透露任何發行人使用AI機器人完成工作的情況,如果沒有虛增銷售收入,請問發行人又是如何完成這樣高達40%幅度的減員增效的?
假設2021年的銷售收入增長率與員工人數增長率相同,則相當于發行人虛增了銷售收入約3.2億元。
(2)發行人的銷售業務主要通過經銷商進行,但報告期內退出的經銷商數量幾乎每年都在增加,對應損失的銷售收入每年也在增加;而新增的經銷商數量每年都在減少,對應新增的銷售收入每年也在減少。最終造成了累計留住的經銷商數量每年都在減少,特別是2021年的經銷商數量減少了52家,退出和新增的經銷商帶來的銷售額基本持平了,這與發行人2021年銷售收入高達24%的增長率對比明顯異常。具體請見下表。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3)發行人的三種主要產品的銷量都在逐年遞增,尤其是2021年的增長幅度顯著增加。但奇怪的是發行人的銷售人員薪酬卻在逐年遞減。以2021年為例,三種產品的平均增長率約30%,但銷售人員的薪酬卻反而減少了10%,兩者差異又恰好約40%。具體請見下表。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發行人的銷售團隊仿佛是鐵軍,薪酬下降了一成,銷售業績反而增長了三成。這樣的逆勢增長也太違背常理了。
不僅如此,發行人三種主要產品中,增長率較大的腎炎康復片和脈管復康片的銷售數量增長率,還明顯高出了對應疾病的增長率,明顯不合理。
比如腎炎康復片的銷量在2021年增長了約32%,但對應的慢性腎病(CKD)在中國的病患增長率僅為15%-17%,發行人的銷量2倍于其增長。
而用于治療糖尿病周圍血管疾病的脈管復康片,在2021年的銷量,則更加離譜地實現了45%的增長率,但對應的糖尿病在中國的增長率僅為2.8%,前者是后者的16倍!如果不是因為懷疑虛增收入,還真要以為中國的糖尿病人突然劇增了45%呢。具體請見下表。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4)伴隨著發行人收入和利潤的持續增長,發行人三大主要產品的多數包裝型號的銷售均價卻持續下降。報告期內,
腎炎康復片45片,從期初的19.17元/盒,逐漸下降到18.94元/盒
腎炎康復片60片,從期初的25.47元/盒,逐漸下降到24.90元/盒
血府逐瘀膠囊24粒,從期初的16.92元/盒,逐漸下降到16.58元/盒
血府逐瘀膠囊36粒,從期初的24.93元/盒,逐漸下降到24.25元/盒
脈管復康片36片,從期初的25.36元/盒,逐漸下降到25.16元/盒
脈管復康片72片,從期初的49.34元/盒,逐漸下降到49.28元/盒
由于發行人終端客戶主要以公立醫療機構為主,上述銷售降價本身符合醫保控費的大趨勢。
而發行人的采購均價并未發現有明顯下降,以采購數量較大的川芎為例,采購均價反而從2020年的19.27元/KG,上漲到2021年的23.37元/KG;數量緊隨其后的地黃,同期也從12.2元/KG上漲到13.76元/KG。
出于嚴謹性,估值之家繼續研究了發行人在報告期內的前10大主要原料的采購均價,發現上漲多于下降。具體請見下表。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通過上表進一步計算出每一項的采購數量,再將采購總金額/采購總數量,得出加權平均后的采購均價。
結果令人驚訝,加權平均后的采購均價,從2019年的1.125元/單位,上漲到2021年的1.341元/單位,上漲了19.2%,這意味著成本均價反而是有較大上漲的。
再結合之前分析過的,發行人銷售數量的不合理大幅增長,可以發現:在銷售均價總體下降、成本均價較大上漲的情況下,發行人毛利率圍繞82%還有小幅上漲是不合理的。如果把銷售數量去除不合理的大幅增長,毛利實現較大增長也是不合理的。
據此,不能排除發行人毛利和毛利率均存在虛增的可能性。
考慮到發行人報告期內存在頻繁且大額的關聯交易行為、以及持續且大額的現金分紅行為,不能排除發行人通過關聯銷售壓貨、現金分紅體外循環的方式進行虛增收入。
比如,天津醫藥集團太平醫藥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均為發行人的關聯銷售客戶,報告期內每年均存在金額過億元的關聯銷售(2019年1.02億元、2020年1.22億元、2021年1.59億元)。
再比如,2018至2021上半年,發行人已經累計進行四次現金分紅,分別為0.7億元、0.69億元、2.43億元、1.0億元,合計高達4.83億元。按控股股東59%的股權計算,控股股東可以分紅約2.8億元。
三、醫保控費、集中采購等多項政策利空,對發行人持續盈利能力構成挑戰
3
醫保控費、集中采購等多項政策利空,對發行人持續盈利能力構成挑戰
按照醫保控費等政策,為了控制醫保支出的不合理增長,國家對于“虛增的量”和“虛高的價”都要作為“水分”擠掉。
而發行人每年都通過高額銷售費用來推動銷量,比如2021年的銷售費用高達5.15億元,是當年凈利潤2.34億元的2.2倍,這其中有多少銷量是用錢硬推出來的?再結合82%的高毛利率,發行人后續的收入和利潤,很可能會受此政策影響。
招股書顯示:“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通過了《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試點方案》。根據湖北省醫療保障局2021年12月27日發布的《中成藥省際聯盟集中帶量采購公告(第4號)》,公司主要品種血府逐瘀膠囊(36粒)入選,中選價格為19.12元。”
而對比發行人同期同樣型號的產品,市場售價卻高達24.93元。也就是說,僅按目前的集中采購砍價力度,就將使發行人的銷售收入減少23.3%。
如果這一方案當年就全面推行,發行人當期的收入和利潤都將出現負增長。
未來,集中采購肯定會從試點轉向全面推行,力度也會不斷加大,直至真正實現靈魂砍價。可以預見,發行人如果沒有及時另辟蹊徑,屆時其收入和利潤都會遭受較大影響,甚至出現斷崖式下降。
招股書還顯示:“目前,公司有11種藥品列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31種藥品列入國家醫保目錄。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和國家醫保目錄會根據藥品的使用情況在一定時期內進行調整,公司產品若被調出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和國家醫保目錄,將會對公司生產經營產生不利影響。”
由于發行人的主要終端客戶是公立醫院,如果發行人的藥物被調整出醫保目錄,則意味著該藥物的主要銷售渠道被終止,肯定會嚴重影響發行人的收入和利潤。
綜合上述分析,發行人在未來面臨較多政策天花板的限制,對其收入和盈利都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4
重銷售輕研發,銷售費用占比超過50%,專利持續空心化,或影響未來產品競爭力
招股書顯示,報告期內發行人的銷售費用居高不下、占比較高,和同期的研發費用對比,有如九牛一毛。具體請見下表。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發行人的銷售收入不但逐年遞增,其對營業收入的占比,都已經在連續增長后突破了50%。
而根據摩爾金融統計,2019年A股全部304家上市醫藥企業中,銷售費用營收占比超50%的,也僅為30家。
珍寶島藥業、步長制藥、康美藥業、和貴州益佰制藥等多家上市公司都曾經因為銷售費用占比過高而收到過上交所問詢函。
同年,因為財務部醫保局聯手核查77家醫藥企業財務問題的消息持續發酵,曾導致整個醫藥股板塊市值,在短短幾天內縮水近2000億,多只個股持續大跌破位,更有天士力創出了六年來的新低。
銷售費用營收占比過高,之所以被多方詬病,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是因為可以合理懷疑這些公司賣的到底是靠藥賺錢,還是靠不當行賄性質的銷售來不斷續命?
發行人如此高的銷售費用和占比,即使成功上市,也依然是一顆風險巨大的“雷”。
但與畸高的銷售費用相反,發行人的研發費用卻畸低,幾乎緊貼著高新技術企業資質所要求的3%研發費用占比的紅線。
作為一家中醫藥老字號生產企業,藥品質量是生命線,而新藥或新品種的研發則代表著未來的發展前景。但發行人如此重銷售輕研發,實有本末倒置的嫌疑。
而輕研發的明顯后果之一,就是新藥新品種的專利研發,數量和質量的不斷下降。
估值之家將招股書披露的所有專利,包括發行人及其子公司,去除掉實用新型和外觀專利等與新藥研發關系不大的項目后,保留全部的發明專利。具體請見下面2張表。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如果對上述29項發明專利,進一步按申請時間歸納,可以發現:
在2003-2005的三年間,發行人共申請了13項發明專利
在2006-2010的五年間,發行人共申請了9項發明專利
在2011-2015的五年間,發行人共申請了3項發明專利
在2016-2021的六年間,發行人共申請了4項發明專利
從發行人申請發明專利的數量上,可以明顯看出逐年斷崖式下降的趨勢
如果繼續分析發明專利的質量,發行人最近一次的新藥發明專利是2011年的“一種用于治療腦梗塞的藥物組合物”,也就是說,最近10年內發行人沒有申請過任何新藥發明專利。
而且,在2012-2021的最近10年中,申請發明專利的含金量也不高,不但沒有新藥發明專利,除了2016年的紫雪散的制備方法(非新藥),其余的5項發明專利都只是檢測方法。具體請見下表。
天津同仁堂深陷商標侵權訴訟,收入、利潤增長“精確制導”并遠超行業,業績真實性存諸多異常,銷售費用率竟
綜合上述分析,發行人重銷售輕研發的畸形結構,最終可能影響發行人未來的產品競爭力。
5
主要產品高度集中,加劇了風險
招股書顯示,發行人的主要收入和盈利,均集中于腎炎康復片、血府逐瘀膠囊和脈管復康片這三大主營產品,三者合計占到最近一期營業收入的88%,毛利的91%。
尤其是腎炎康復片和血府逐瘀膠囊,合計占比約80%,發行人對其存在高度依賴。
一旦這兩三種主打產品隨著競爭加劇而遇到有力的競品,或者隨著技術進步而出現替代品,發行人的業務都將受到重大影響,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6
涉及產品質量問題等多項處罰
報告期內,發行人曾因產品質量等問題涉及多項處罰。
比如,發行人2020年曾因生產的元胡止痛片檢測出金胺O被行政處罰。
金胺O又名堿性嫩黃,屬于工業染色劑,對人體具有一定毒性作用,人接觸或者吸入金胺O會引起中毒,長期過量食用易損傷肝腎。2008年就被衛生部列為非食用物質的“黑名單”,在中藥材、中藥飲片和中成藥中均不得檢出。但實踐中還是有發現金胺O被用于劣質黃柏、蒲黃、延胡索等中藥材、中藥飲片的非法染色。
由于金胺O屬于有毒有害物質,發行人的這一違規事件的性質甚至與產品質量事故有關,其內部控制、尤其是產品質量的控制還有待加強。
資本市場和投資者對于醫藥企業的產品質量非常敏感,如果上市后爆出類似的問題,股價必然面臨跳水而帶給投資者損失。
值得一提的是,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張彥森,還是天津著名的食品企業狗不理包子的董事長。
據相關媒體報道,狗不理包子自2012年開始,本末倒置、過于追求高利潤率,反而輕視了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倒掛的性價比被顧客用腳投票,營業額一落千丈,不但沖刺IPO失敗,而且退出北京市場,并面臨瀕臨倒閉的風險。
希望本次天津同仁堂的IPO沖刺之旅,能用熟悉的配方,做出不一樣的味道來。
推薦閱讀:






.png)
.png)
.png)